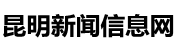回顾中国科幻的迅速发展历史,在20世纪初时代的巨大变化中,中国科幻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类进步的梦想中汲取“原力”,融合了民族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主义精神。 20世纪末、21世纪初,刘慈欣将其发扬光大,谱写了中国气派的“星空浪漫主义”,鼓舞了我们,使中国科幻走向世界。 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百年罕见的大变局”是如何引起科幻艺术的新变化的呢?
那种提高、追求进步的精神体现在哪里,科幻的种子生长在哪里
年末,世界科幻迷听到了一个悲伤的消息。 美国时间12月23日,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学者詹姆斯·甘去世,享年97岁。 冈恩氏选择的读本《科幻之路》启蒙了数不胜数的网民。 199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成为许多中国网民了解世界科幻的重要指南。 他的另一部着作《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系统地阐述了科幻文学的由来和演变。 这本书于1975年初版,直到今年才发售中译本。 尽管时隔45年,但还是很兴奋。
癌症出生于1923年,比世界第一本专业科幻杂志雨果·根斯巴克创立的“惊奇故事”早三年。 他经历了20世纪美国科幻文化的繁荣和起伏变迁,对任何重要的作品、杂志、人物都很了解,与许多著名作家有着更深的交流。 这是因为谈论历史时会像家珍一样。 另一方面,癌症从1970年开始在大学开设科幻课。 《交错的世界》是根据他的演讲稿修订的,既确保了学术水平,又能理解晓畅,而此前翻译到国内的科幻史类著作多少带有学院派的深奥。 特别令人钦佩的是,以中译本的出版为契机,已经90岁的冈恩先生不仅根据原书改写了第一章,追记了最后一章,特别提到了《三体》英文版的获奖等最近的事情,从而使这部经典科幻史的著作在结构上更加完善。 这样的观点尤为宝贵,毕竟冈恩和同时代的许多科幻大师早就去世了(本书第一版序言的阿西莫夫于1992年去世),近一个世纪的科幻风景,可以说整合成了冈恩那里一贯深刻的生命体验。

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冈恩开宗明义指出:“科幻小说是变化的文学,它本身就是变化的最佳例证。” 围绕“变化”的核心概念,冈恩生动地描述了科幻的历史: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通过理想国的描写、虚构的旅行到达奇妙世界的故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的生产方法、生活态度、战争模式等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科学革命 新的信念确立了。 人类不需要依赖超自然力量,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探索未知,认识宇宙、自然、自我,通过自己的发明改变命运,获得更好的生存能力。 在这一信念下,科技发明日新月异,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取得了惊人的物质成果,还重塑了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未来”取代了已经失去的“过去”,成为了“黄金时代”的新坐标。 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变化,为科幻小说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定义科幻小说的唯一标准可能就是其态度。 科幻小说包含了宇宙已知的基本概念。 人类的使命是了解宇宙,发现宇宙和人类从哪里来,如何进化到今天的状况,宇宙和人类去哪里,什么样的法则制约着它们,最终所有的结局会怎么样,以及如何结束。
换言之,最先有一个新奇的故事,世界人才不是知道“科学幻想”,而是在渴望、探索真理、走向新的、未来的整体氛围中,科幻小说时有发生,这种因果关系应被视为“科幻小说是科幻世界的文学” 因此,癌症在刻画不同阶段科幻小说的快速发展时,尤其注重证明当时的科学成果及其社会影响。 对许多科幻迷来说,这是了解科幻小说的重要入口,通过展示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魔法变化和未来无限的可能性,科幻为网民提供了最重要的快乐。 这种快乐被刘慈欣比喻为“科幻的力量”,可以把所有幼稚粗糙的故事催化成迷人的精神食粮。 可以说癌症的科幻史是“原力”的消长史。 读了这段历史,网民可能记不住很多感兴趣的细节,但一定会在哪里出现追求进步的精神,给人留下科幻种子在哪里生长的深刻印象。

例如,19世纪相继出现新发明,使凡尔纳在欧洲登场。 这位法国天才感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召唤,成功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小说的主题。 他所描绘的令人向往的新发明,往往基于以前人所持的技术构想,可以让网民相信未来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故事。 虽然当时还没有“科学幻想”的概念,但凡尔纳回应了欧洲人面对科学奇迹时的狂喜,在世界范围内也取得了成功。 到了20世纪,不满足于现状的科幻精神在美国这个新殖民地繁荣起来。 随着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崛起,世界各地优秀人才对这里的凝聚和大众对通俗读物的诉求不断增加,科技时代探索未来奇景的出版者顺应时势,通过图书和杂志凝聚了具有共同兴趣的作者和网民,成为科幻“黄金时代”, 冈恩氏自豪地写道:“科幻小说虽然出生在法国和英国,但在美国发现了自己。” 到了20世纪60年代,来自英国、在美国得到响应的“本潮”运动,开始改革创新科幻的美学面貌,新一代作家广泛借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史诗的妙技,大胆开拓新的主题素材,包括对人的身体和其他隐私行业的探索。 在许多人看来,这些作品为了得到“主流”文化界的认同而牺牲了故事的可读性。 冈恩氏指出,老派科幻迷抵制“本潮”科幻,根本原因不是模糊文学的妙招,而是视点的变化。 “本潮”作家从以往科幻文学那样广阔的时空尺度审视人类命运,相信理性和科学推动我们前进的态度,将眼球聚焦于当今社会和个人的烦恼,采取了主观主义、非科学、感觉。”无论网民持何种态度 这一变化让冈恩在初版结束时总结历史,在展望未来时深刻指出。 科幻的感人之处在于“傲慢谦虚的哲学”。

冈恩氏对数百年科幻史的记述和把握,可以说是用完全纯粹的科幻迷的角度,对科幻风尚的一些变化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因此刘慈欣称赞这本书为“目前国内翻译出版的唯一从科幻角度撰写的科幻文学史”。
刘慈欣和他的《三体》资料照片
《交错的世界》詹姆斯冈恩着资料照片
清代吴仪人的科幻小说《新石头记》资料照片
鲁迅翻译的凡尔纳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的资料照片
在时代的巨变中,中国科幻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类进步的梦想中汲取了“原力”
当然,作为1970年代完成的著作,《交错的世界》也有其局限性。 它基本上以英美科幻为主体。 这可能符合历史现实,但也向今天的中国网民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书中的一段令人感慨:
到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见证了工业革命的考验和胜利,接受了科学引导人类走向新的、更好的生存状况的社会理念。
美国学者写道,这是一个闪耀金黄色的历史时刻。 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变化正在加速,世界正在为科幻小说的到来做准备。 但是,1840年不能不唤起中国人痛苦的记忆。 对我们来说,“渴望真理”、“勇敢探索”、“新”、“走向未来”、“理性精神的迅速发展”只是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的一个方面,但在故事的另一个方面,探索未知的领土与殖民者的暴力征服密切相关。 正是殖民主义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急剧的“变化”,促使了科幻小说在中国的生根发芽。
任何文明都要持续快速发展,必然要经历自我肯定、自我保留和自我质疑、自我改革创新的往返,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统一。 新旧文明的激烈冲突也带来文学艺术的重要变化。 当西方文明肯定和质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科幻的“原力”也向两个方向发生了动荡。 对“进步力”的赞扬(凡尔纳等)和对“破坏力”的担忧(弗兰肯斯坦等),两者的交错连接着科幻的历史。
同样,中国科幻诞生于本土文明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 19世纪,曾经的天朝上国逆转了作用,成为后进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西方文明”的“进步力量”在后进国家面前变成了“毁灭力量”,这种势头的历史动能给落后者们提出了自我残留和自我变革平衡的难题。 另一方面,否定以前流传下来的激进的变革意志也是从这里来的。 在这场变革中,基于现代科学改造国民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成为重要的文化事业,“小说”的作用被提拔,“小说界革命”中自然出现了科幻小说的身影。 在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上,主编梁启超翻译了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里昂的《世界末日记》,讲述了数百万年后人类文明逐渐凋零的故事。 结合梁先生当时的宗教思想,他翻译这部科幻小说的目的是展示天文学尺度上的末日形象,让国民可以改变好恶和死亡,放下对红尘的贪婪,勇敢、刚毅,投身于舍命取义的英勇事业。 呼应以身殉职的挚友谭嗣同,在后者中,人与人、人与万物的隔阂带来了世间的不幸,通过“以太”这一物理学家所设想的普适宇宙的媒介,个人的诚信能够感动他人,冲破彼此的隔阂。 英勇牺牲的时候,他一定期待着自己的死能唤起越来越多的人的热血。 他还设想,既然人类的进化无法停止,总有一天要摆脱肉体的束缚,成为纯粹的精神存在,在宇宙中漫游。 换言之,是现代科学推进的三观革命,赋予了仁人志士舍伸张正义的勇气。

另一方面,这种英雄气概又与国际主义精神融合在一起:先知们不仅要拯救自己的民族,还必须为人类和平共处铺平道路。 24岁的梁启超这样坦白。 “我们的宗旨是传教,也是非当政。 拯救地球和无量世界的众生,也不是拯救一个国家。 ”。 这意味着,不仅要以西方文明为鉴改革创新自我,还必须以自身困境为切入点思考西方文明的弊端,在东西方相互鉴中为人类文明寻求新的价值和方向。 因此,中国科幻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科幻的影响和启发,在模仿和改写的尝试中探索自己的道路。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被梁启超改造成后世皆知的“睡狮”,发展成了包含“破坏力”在内的文学形象富有“进步力”的民族寓言。 其实阴差阳错(学术界早有考证)。 吴赢人的《新石头记》让贾宝玉脱胎于20世纪初的中国,在经历了社会的黑暗之后,将进入科技发达、道德善良的“文明境界”。 其中乘坐飞车、驾驶潜水艇的部分明显模仿,调戏维尔纳的故事,全景式的乌托邦描写也有爱德华·贝拉米《百年一觉》的影子,但作者的意图绝不是拙劣的模仿,而是通过科幻。 对此,翻译凡尔纳的青年鲁迅也深有感触。 之后,他不再热衷于科幻小说,但在《破坏声论》中对“黄祸论”的看法也和中国科幻小说中偶尔出现的黄种人打败白人的复仇幻想一样。 未来的中国强大了,就不应该走列强的老路,而应该扶助弱小,摆脱奴役,获得自由。

总之,近代中国虽然饱受欺凌,但在顽强的求生意志下,奋发图强的精神和英雄主义气质,这种精神和气质受到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的激励,为美好未来的信念和信念而牺牲。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科幻也在时代的巨大变化中,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类进步的梦想中汲取了“原力”。 当然,科幻文艺的繁荣归根结底必须以综合国力为坚实的基础,法、英、美、苏、日等国科幻的迅速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直到20世纪末,才出现了凭借《鲸鱼之歌》登上历史舞台的刘慈欣。 2006年,《三体》开始连载。 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出版,开始在科幻圈之外引起轰动。 从1999年到2010年,这是刘慈欣个人成长的阶段,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阶段,是中国高校开始扩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基数逐年增加的阶段,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最终在2010年首次迎来城市人口过半 这样的历史性变化为中国科幻小说的蓄力提供了能量,为《三体》的成功奠定了文化土壤和大众的基础。 在“变化”和“原力”的视角下,我们可以发现刘慈欣的故事中蕴藏着一个多世纪的苦闷和追求,他们挑起着一个民族内心深深的焦躁和渴望。

首先是强烈的进化压力和生存焦虑。 长期居住在山西姑娘关的这位工程师小说家坚持科学探索,特别是对基础科学取得划时代进展的期望,对于人类不能永远停留在地球上,为了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必须进入宇宙的信念,为了在极端的条件下保全整个文明,许多反道德的 在《乡村教师》中,身患绝症的老师在临终之际还背负着无知的孩子们无法理解的牛顿力学三大定律。 出乎意料的是,上帝常规的外星文明在打扫战场时鉴定了沿途行星的文明水平,随机被提取为地球样本的孩子们面对一系列测试问题都无动于衷,表明只有正确地回答牛顿定律,地球才值得生存。 用奇异的方法,作家再次表达了对文明降级后失去生存资格的古老担忧。 有趣的是,100多年前在商务印书馆翻译的凡尔纳小说《绕月》,中、地、月运动属于《三体问题》。 在原着的另一部翻译《月界旅行》中,译者周树人在序言中推测:如果人类能够殖民外星,“地球大同是可能的,但行星上的战祸还会发生。” 从鲁迅到刘慈欣,对生存和灭亡的思考始终位于百年中国科幻的核心。

其次,通过超感官冲击促使三观改造,完成文化的改革创新。 年轻时第一次读完克拉克的《2001 :太空漫步》后,刘慈欣感受到了“对宇宙宏伟神秘的深深敬畏”。 他说,科学描绘的宇宙形象远比科幻小说震撼,科幻作家只是通过小说“翻译”了这种冲击,并传播给了网民。 在随笔中,他说希望所有忙碌的人通过科幻停下匆匆的脚步,仰望星空,感受宇宙的浩然。 在小说中,他试图用现代汉语展示宇宙观尺度,使我们有限的个人经历和喜怒哀愁受到了超感的冲击。 在最极端的《朝闻道》中,科学家以生命为代价换取认知科学真理的十分钟。 在历史的参照系中,经常描绘地球末日、太阳系末日甚至宇宙末日的现代作家,与20世纪初翻译《世界末日记》的梁启超一样,试图通过文学工作推进民族精神的更生。

然而,刘慈欣的故事看起来暗淡,人类在宇宙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但因为能认识“真理”而伟大,因为进取而崇高,因为失败而悲壮。 因为这种悲壮,是人类生存意志和种族尊严的表现,营造出英雄主义的气氛。 这在《流转的地球》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太阳系发展成红巨星的灾难,应该发生在几十亿年后,但小说家降临极速,在危机和处理危机的手段之间造成了巨大的不匹配:人类为了在地下世界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让地球远离太阳系,以这样笨拙的方式逃亡。 在茫茫冰雪覆盖的地表上,庞大的工业系统难以维持运转,表现出人类的国际合作精神和顽强的抗争意志。
总之,刘慈欣小说对生存的不安、对进化的执着、对科学的崇拜、人类团结合作谋求文明延续的向往,是近代中国核心命题在星际尺度上的重新表现。
刘慈欣将民族英雄风骨投射到未来时空,谱写了中国气派的《星空浪漫主义》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了不起的人物,留下了歌曲和泪水的事迹,通过历史记录和文学艺术的演义,成为世代相传的集体记忆,塑造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的理解和感情。 例如“易水寒以风萧萧,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就是壮士悲歌。 例如“安能弯下腰来权力大,讨不到我喜欢”,这就是盛唐气象的文人风骨。 例如义薄云天、不畏豪强的关云长,就是普通人对忠义的寄托。 例如“大河波涛辽阔,风吹稻花香两岸”,既是为保卫家乡而流血牺牲的气魄,也是为建设家乡而翻天覆地的气魄,更是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期待。 这些故事都灌溉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培养了民族自豪感,在艰难的时代给了我们勇气。 刘慈欣小说的魅力之一,就是将这样的英雄风骨投射到未来的时空上。

如果,在20世纪的中国大众文艺谱系中,金庸塑造了一系列古代中国英雄,“历史浪漫主义”,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塑造了一系列现代中国英雄,“革命浪漫主义”,刘慈欣塑造了一系列未来中国英雄,“星空浪漫主义” 好莱坞电影的习性是在《三体》出现之前,美国黑白英雄拯救世界。 通过恢宏的设定、庞大的骨骼、众多复杂的故事,刘慈欣临摹了未来的人物群像。 其中有史强一样强悍狡猾的警察,章北海一样冷酷的决断,周密隐忍的太空军政治委员,引发危机的叶文洁和力量挽回狂澜的罗辑。 这些人物在涉及命运时的选择,让网民开心,争论不休,像谈论赤壁之战一样谈论地球宇宙舰队是如何被三体人的“水滴”探测器破坏的,像谈论荆轲刺秦一样为了章北海改变未来太空军的快速发展方向, 就像讲述肖邦为宋辽兵在雁门关外自杀一样,罗辑在荒郊讲述三体人,相互威胁不让对方放弃侵略,金庸的成功不仅是因为他熟知以前流传下来的文化,还因为他写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刘慈欣的成功也不仅是因为他奇妙宏伟的技术想象,也因为他写下了中国伟大的星空浪漫主义。 通过振奋人心的虚构瞬间,将我们古代、现代、未来的中国英雄的想象联系起来。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全民科学素养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许多过去的科幻场景已经成为现实。 当今人民群众对科学技术话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更关心宇宙时代人类的命运。 刘慈欣为这样的网民讲述了古老农耕民族的觉醒和新生,谱写了人类在宇宙时代的荣誉和梦想。

当然,这绝不是刘慈欣的作品完美无缺。 相反,以最高的艺术标准衡量,他的小说有明显的不足。 这很正常。 在由古代神话、庄子寓言、屈原赋、李白诗、东坡词等创作的华夏文学长河中,伟大浪漫的心灵一次次演奏出生命的律动,创造出许多不朽的篇章,但科学革命后时空的、探索的艰辛、技术的广博、现代中国人的豪迈 刘慈欣的作品是中国作家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探索后取得的阶段性成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也衬托出了中国科幻整体实力的相对单薄。
现在有必要考虑这些问题。 我们所处的“世界百年不遇的巨大变化”是如何引起科幻艺术的新变化的? 在科幻与现实的对比下,中国的科学幻想应该如何理解自己现在的状况,思考未来的道路? 能够刻画出时代脉搏,诉说人们内心深处的忧患和憧憬的作品会怎么样呢? 当广阔的胸怀、进取的豪爽、勇敢的勇气、追求真理、为人类福利奉献的决心等曾经闪耀科幻的核心精神凋零于世界各个角落的状态下,我们将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果中的“原力”,实现民族精神的繁荣,实现人类的进步。 愿我们努力前进,用癌症的话不断提醒自己。
科幻小说就像来自未来的信,写信的人是我们的子孙,敦促我们保护他们的世界。
标题:快讯:在时代巨变中追寻中国科幻的“原力”
地址:http://www.kwan-yin.com.cn/kmjy/912.html
心灵鸡汤: